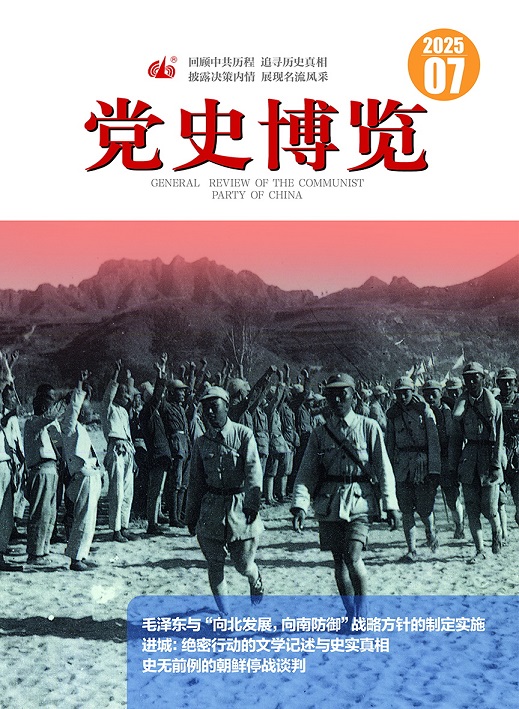■瞿秋白“不得不留”的原因■
那么,当时瞿秋白是否就是因为博古或博古们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他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即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组织局,相当于后来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和陈云。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人和论者所说的,谁去谁留的生杀大权操于博古一人之手。
诚然,博古自己也在1943年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过:“当时三人团(博、李、周)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三人团”是1934年夏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的,负责筹划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最高决策机构。博古分工负责政治,因而他要对干部的处理负全责。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一定搞了宗派主义,借机“抛弃”瞿秋白,置他于死地了吗?假如我们不是从“博古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王明团伙’的副帅”的既定概念出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就会更客观、更准确。
前面已说到,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对瞿秋白的留下,也应当这么看。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艺术局负责人、《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以及他一向具有的理论、宣传特长是吻合的、相称的。尤其是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这个细节,也是由朱德在1937年春对史沫特莱披露的。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有人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例说,既然博古能安排他们坐在担架上走完长征,为什么不能同样安排瞿秋白坐担架长征呢?这不是博古有意“抛下”他不管,而任其死去吗?抱这样一种想法的人委实有点小儿科。殊不知各人情况不一样,不好简单类比。若以毛、王论,其一,毛泽东一向被说成是博古的头号打击、排挤对象,而王稼祥也在此前已与博古发生分歧。博古却不管这些,依然让他们享受特别照顾,参加长征。这不正好说明博古在高级干部去留问题上,没有搞宗派主义吗?其二,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且在红一方面军中有着极深而广的人脉关系;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作为红军长征最高领导、指挥机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和王稼祥自应被抬着去长征。而瞿秋白没有这种必要性,有另外的重要工作等着他去做。其三,毛泽东往往因为焦虑、气不顺和劳顿过度而生病,病情相对和缓平稳;王稼祥主要是枪伤及肠,病情也相对平稳。而瞿秋白的肺病则凶险得多,因此他身上随时带着青霉素应急。像瞿秋白这么一个病人,谁能打包票说他一样能安全坐担架走完长征?
有人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延安时期的相关回忆,以及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在多年前的相关回忆,证明博古阻挠瞿秋白参加长征。张回忆说,长征前“高级干部(的去留),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他要求同走,他表示同情,便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吴的回忆说,他听到“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走,心里很难受。一方面请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改变决定),毛泽东说他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一方面向张闻天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这两个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第一,无论是张闻天的回忆,还是吴黎平的回忆,都明白无误地说明:长征前夕高级干部的去留,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第二,博古在组织上决定高干的去留后,不管何人来说,都不再作有违组织决定的改变,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当然,因为这一点,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他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正好给他的“黑面木偶”的外在形象,作了本质方面的注脚。
最后,瞿秋白在得知自己被留下时的反应,尤其是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而积极以至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时的出色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他被抛弃的说法。
在瑞金和瞿秋白是“挚友重逢”的吴黎平,长征前夕曾请秋白到他家吃饭。其时瞿秋白已经知道自己被留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对曾经朝夕相处而今一旦分别的战友、同志,不免有很浓的离情别绪。然而,这情绪加酒劲并没有使他消沉。吴黎平回忆道:“他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瞿秋白的这番表白,无疑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应视为他对自己被留下坚持斗争的理解和自觉执行。这既有他的一贯言行实践可以作证,更有他此后的斗争业绩和风范可以说明。
■瞿秋白等英勇就义,博古不得不说了违心的话■
1935年2月11日晚,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人化好装,离开瑞金向赣闽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不料竟被敌人捕获。因不屑卖身投敌,他最后遭敌毒手,英勇就义于长汀罗汉岭。有人又把他的死,归咎于博古没有带他长征。这显然不公平。
瞿秋白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成人后即抱改造社会之志。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便去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俄国,次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他很早就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终生实践之。他深知,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如此尖锐、剧烈的社会革命,无疑要有一部分自觉的牺牲者。瞿秋白自己就甘心做这样的牺牲者。为了理想,“他能够毅然决然抛弃属于他的原来的阶级的一切——温暖的家庭,相当优越的地位,对于旧的事物(如做旧诗词和刻图章之类)的癖好——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士,转变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到最后为无产阶级而贡献他的生命”。无论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做着苏维埃的各项事情,瞿秋白都以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忠诚,奋不顾身。他在突围转移途中被敌人捕获后的表现,是他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与体现。
瞿秋白被俘后,敌人曾用尽手段对他“软化”,企图让他“归顺”。但他坚贞不屈,敌人终于忍耐不住。1935年6月2日,蒋介石给蒋鼎文发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是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瞿秋白被囚以后,各方纷纷营救。起初蒋介石惮于民意,不敢遽然加害。但此事被日本获悉,认为瞿秋白是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其声望又高,如果不加杀害,为日后一大隐患。日本便施以“以华制华”的毒计,要挟蒋介石杀害瞿秋白,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蒋介石获悉以后,极为恐惧。其御用文人戴季陶,则是火上浇油。他平日对瞿秋白揭露他破坏民族战线的罪恶阴谋一直怀恨在心,因而大肆叫嚷“瞿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于是,蒋介石便密令蒋鼎文杀害瞿秋白。后因陈立夫派人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劝降,延缓了行刑的时间。读了这段文字,瞿秋白死于何人之手,已然昭昭。
有人以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被留下的人都牺牲了,而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走了的人都活下来了为由,指责博古,说他明知留下是死路一条,却偏要瞿秋白留下。这也有失公允。博古在1943年9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所作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曾郑重声明:“对这批人(即项英、潭秋、秋白、陈毅、何叔衡等)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博古的这番心迹坦露,完全可以视为对上述诘难的回应。说实话,当时“去”和“留”都前程难料、吉凶未卜,因而林伯渠在他的《别梅坑》诗里才有“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项英甚至对留下坚持斗争表现乐观,而对作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表示担忧(当然,这也表现了项英的高尚)。瞿秋白等革命先烈血洒苏区,不消说令人悲伤抱憾。而8万多红军将士经过长征至陕北不足万人,难道就不一样教人唏嘘扼腕吗?
在长征前夕高级干部去留名单的确定上,博古行使了中央赋予他的权力。有些留下,可能不合适,或者当时认为合适而事后证明不合适。即便如此,也不能证实博古借机搞宗派主义、甩包袱、“借刀杀人”。平心而论,换了谁去主持这项工作,也难免出现类似问题。博古所谓“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其实很难办到。就当时形势而言,要么不设领导、指挥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把原本要留的高级干部都带出来;要么另选一批高干留下,替代他们。但是,无论照前者办,还是照后者办,都不能达到中央预设的目的,而且同样避免不了部分同志的牺牲。由此看来,博古在这里不得不说了违心话。■